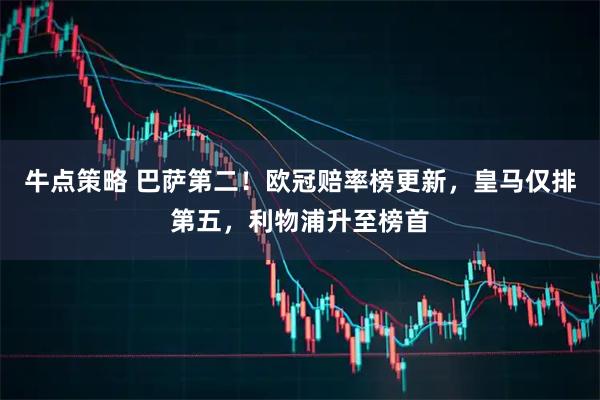那年我22岁信康优配,第一次坐绿皮火车,咣当了三十多个小时,终于从我们那个连名字都土得掉渣的小县城,颠到了深圳。
出站口那股热浪夹着海腥味和尾气味儿,像一巴掌直接把我扇懵了。
人,到处都是人。拖着箱子的,背着大包的,脸上表情都差不多,一半是憧憬,一半是茫然。
我攥着口袋里我妈给的、凑起来的三千块钱,感觉自己像一粒被风吹到水泥地上的沙子,渺小,而且硌脚。
按照老乡给的地址,我七拐八拐地钻进了白石洲。
那地方,后来他们管它叫“深漂第一站”,但在当时的我看来,那就是个巨大的、密不透风的迷宫。
握手楼之间漏下来的天光,跟刀片似的,又窄又亮。空气里永远飘着一股复杂的味儿,炒辣椒的香,下水道的臭,还有洗发水的廉价香精味,全混在一起。
我租的房子在八楼,没电梯。
房东是个叼着烟的本地阿姨,眉毛纹得发青,指着那个不到八平米的单间,言简意赅:“一个月八百,押一付三,水电另算,网自己拉。”
我心里咯噔一下,三千块,这么一下就没了三千二。但我还能说啥?
我说:“阿姨,能不能……能不能先付一个月?”
她眼皮都没抬,吐了个烟圈:“后生仔,这里不讲价的。没钱就住天桥底咯,那里不要钱。”
我把牙一咬,把钱点了给她。
那一沓带着我体温的钱递过去的时候,我感觉自己的一部分也被抽走了。
房子里只有一张吱呀作响的铁架床,一张掉漆的桌子。窗户对着别人家的厨房,油烟味儿直往里灌。
我把行李一扔,整个人瘫在床上,盯着发霉的天花板。
深圳,我来了。
然后呢?
然后就是地狱模式的找工作。
我在人才市场买了一沓简历模板,一块钱一张,填上我那个三流大专的学历和几乎空白的工作经验,开始海投。
人才市场里比火车站还挤,汗味、烟味、廉价香水味熏得人头疼。
每个招聘台前都围着一堆人,HR们个个像皇帝选妃,眼神挑剔又麻木。
“我们这个岗位要求985、211。”
“你有相关工作经验吗?没有?下一个。”
“你期望薪资多少?四千?我们这里实习生只有两千五。”
我一次次挤进去,又一次次被挤出来,手里的简历越来越少,心里的窟窿越来越大。
有天晚上,我灰头土脸地从外面回来,兜里就剩最后五十块钱了。路过一个天桥,底下有个算命的摊子。
一块破布,上面画着太极八卦,摆着几本发黄的旧书。
算命先生瘦得像根竹竿,山羊胡,戴个墨镜,很有“大师”风范。
我本来是不信这些的。
但我那天真的走投无路了。
就像一个快淹死的人,哪怕是根稻草,也想伸手順便捞一下。
我鬼使神差地走了过去,在他面前的小马扎上坐下。
“先生,看看。”我说。
他抬起墨镜,露出一双浑浊但似乎能看穿一切的眼睛,打量了我几眼。
“看相还是算八字?”
“算……算前程吧。”我声音小得像蚊子哼。
他让我报了生辰八字,掐着指头念念有词,半天,突然眼睛一亮。
“咦?”
他这一声“咦”,把我心脏都提到了嗓子眼。
“先生,怎么了?是不是……很差?”
他摇摇头,又点点头,表情神秘莫测:“小伙子,你这命格,奇特啊。”
“前半生是潜龙在渊,苦得很。但是……”他话锋一转,压低了声音,“你时来运转了。”
我愣住了。
“从现在算起,三个月。”他伸出三根枯瘦的手指,“三个月内,你必有横财降临。”
“不是小财。”他加重了语气,“是能让你翻身的大财。”
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,骗子。
这套路太老了。先抑后扬,给你画个大饼,然后让你掏钱消灾祈福。
我站起来就想走。
“你不信?”他叫住我,“我今天给你算,分文不取。你若真发了财,到时候再来谢我。”
我停下脚步,回头看他。
天桥上车流不息,灯光闪烁,他的脸在光影里显得特别不真实。
分文不取?
这年头还有这种好事?
“你记着我的话就行。”他摆摆手,重新戴上墨ঠি,“缘分到了,财自然就来了。”
我将信将疑地走了。
回到那个八平米的出租屋,我把最后一份泡面泡上,闻着那廉价的香精味,脑子里全是算命先生的话。
三个月,发大财。
我自嘲地笑了。
我要是能发大财,还会在这儿啃泡面?
但那句话就像一颗种子,不受控制地在我心里扎了根。
尤其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,每当我被现实揍得鼻青脸肿的时候,它就会偷偷冒出个芽来。
我开始更疯狂地找工作,销售、客服、传菜员……只要能给钱,我什么都愿意干。
有一次去面试一家卖保健品的公司。
经理是个油头粉面的中年男人,唾沫横飞地讲了两个小时的“财富梦想”,说他们公司的产品能包治百病,只要加入他们,半年买车,一年买房。
我看着他那双闪着精光的眼睛,突然想起了算命先生。
这不就是另一种形式的算命吗?
只不过一个说的是虚无缥ove的“横财”,一个说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“提成”。
我没去。
我骨子里还是有点读书人的清高,或者说,是胆小。我知道那是个坑。
钱越来越少,我开始一天只吃一顿饭。
晚上饿得睡不着,就喝自来水充饥。
隔壁住了个在工厂打工的老哥,叫老刘,人不错,有时候会多炒个菜叫我过去吃。
他总说:“小陈,别急。深圳这地方,只要肯熬,总有出头之셔。”
我嘴上应着,心里却在倒计时。
离算命先生说的三个月,还有两个月。
还有一个半月。
一个月。
我的希望,随着日子的流逝,从最开始的嗤之以鼻,到后来的半信半疑,再到最后的孤注一掷。
我开始觉得,那可能是我唯一的指望了。
我甚至开始留意路边的彩票站,每次路过都忍不住多看两眼。但摸摸口袋,连买一注彩票的两块钱都舍不得。
万一,万一那笔横财,需要我自己去“碰”呢?
这个念头一旦出现,就再也压不下去了。
我开始留意各种“偏门”的消息。
同住一层楼的,有个在华强北混的小子,叫阿飞。染着黄毛,手臂上纹着一条不知是龙是蛇的玩意儿,昼伏夜出,看着就不像正经人。
有天我实在撑不住了,找他借烟抽。
他递给我一根,斜着眼看我:“兄弟,看你天天愁眉苦脸的,工作还没着落?”
我点点头,猛吸了一口,差点被呛得背过气去。
“想不想搞点快钱?”他神秘兮兮地凑过来说。
我心里一动。
“怎么搞?”
他嘿嘿一笑:“路子多的是。就看你胆子够不够大。”
他跟我说,华强北那边,有的是“机会”。比如帮人带货,就是把一些新出的、没交税的手机,从香港那边背过来。一次能赚好几百。
“这……这是走私吧?”我有点害怕。
“说什么呢!这叫‘水客’,懂不懂?撑死胆大的,饿死胆小的。你看看我,不也活得好好的?”他拍拍胸脯。
我犹豫了。
好几百,对我来说是救命钱。
但万一被抓了呢?我妈要知道,非得气死不可。
阿飞看我犹豫,不屑地撇撇嘴:“行了,看你这样子就不是这块料。当我没说。”
他走了,留下我一个人在楼道里,烟头明明灭灭。
“横财”,难道指的就是这个?
我一夜没睡。
天亮的时候,我做了个决定。
我不能走那条路。
我爸死得早,我妈一个人把我拉扯大,供我读完大学,她最大的愿望就是我能堂堂正正做人。
我不能让她失望。
我决定,再给自己最后一次机会。
我把身上最后的钱信康优配,拿去打印店,把简历重新设计了一下,看起来更专业。然后,我去了深圳最高级的写字楼区——福田CBD。
我告诉自己,要去就去最好的地方。就算死,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。
我在那些玻璃幕墙的大厦下面,站了很久很久。
阳光刺眼,照得那些大楼像一座座不可逾越的山。
我穿着那件唯一的、洗得发白的衬衫,感觉自己和这里的一切都格格不入。
一个保安走过来,用怀疑的眼神看着我:“干什么的?”
“我……我来找工作。”
“有预约吗?”
“没……没有。”
“那不能进去。”他摆摆手,像赶苍蝇一样。
我站在大厦门口,看着那些穿着精致套装、踩着高跟鞋、走路带风的白领们刷卡进去,心里说不出的酸楚。
凭什么?
他们和我,到底有什么不一样?
那天下午,我没再投简历,就坐在市民中心的台阶上,看着远处的地王大厦和京基100。
我想我妈了。
我想我们家那个破旧但温暖的小院子了。
我想,要不算了吧。
回老家,找个安稳的工作,一个月两三千块钱,也够活了。
我掏出手机,想给我妈打个电话。
就在这时,一个电话打了进来。
是个陌生号码。
我犹豫了一下,接了。
“喂,你好。”
“你好,请问是陈驰先生吗?”一个很干练的女声。
“我是。”
“这里是XX科技有限公司,我们收到了您的简历。请问您明天上午十点,有时间来我们公司面试吗?”
我当时脑子“嗡”的一下,一片空白。
我投过这家公司吗?
我完全没印象。
我结结巴巴地问:“请……请问,是哪个岗位?”
“总裁助理。”
我差点把手机扔出去。
总……总裁助理?
开什么国际玩笑?
我一个三流大专生,去应聘总裁助理?这不是把我当猴耍吗?
“您……您是不是搞错了?”
“没错的,陈驰先生。地址我稍后会短信发给您,请您准时参加。”
对方说完,就挂了电话。
我捏着手机,愣了足足有五分钟。
这是一个骗局。
绝对是。
不是骗我去搞传销,就是噶我腰子。
我第一反应就是不去。
但那个地址,我查了一下,就在我眼前的这片CBD里,一座非常气派的写字楼。
我心里那个叫“侥幸”的魔鬼,又探出了头。
万一是真的呢?
万一,这就是算命先生说的那笔“横财”呢?
我决定去看看。
就算被骗,我也认了。反正我已经一无所有了。
第二天,我把我那件最体面的衬衫又洗了一遍,用矿泉水瓶子装满热水,把褶皱的地方烫平。皮鞋擦得能照出人影。
我提前一个小时就到了那栋写字楼下。
我不敢进去,就在楼下的花坛边上坐着,紧张得手心全是汗。
九点五十,我深吸一口气,走进了那扇旋转门。
前台小姐姐人美声甜,确认了我的信息后,给了我一张访客卡,让我去32楼。
电梯飞速上升,我的心也跟着悬到了嗓子眼。
32楼,一整层都是这家公司的。装修得非常现代化,视野开阔,能俯瞰大半个深圳。
一个穿着职业装的女士接待了我,就是昨天给我打电话的那位,她自称是人事经理,姓李。
她把我带到一个小会议室,给了我一杯水,让我稍等一下。
我坐在柔软的皮椅上,看着窗外的云,感觉像在做梦。
过了大概十分钟,门开了。
走进来一个男人。
他看起来四十岁左右,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休闲西装,头发梳得一丝不苟,戴着一副金丝眼镜,气质儒雅。
但他一开口,我就觉得不对劲了。
“陈驰,是吧?”他的口音,带着一股我们老家那边特有的味道。
我猛地抬起头。
他也正在看我,眼神里有一种我说不出的复杂情绪。
“你不认识我了?”他笑了笑,“也难怪,都十几年了。”
我脑子里飞速旋转,搜索着所有可能的记忆。
这张脸……有点熟悉,又很陌生。
“你是……?”
“我叫林海。”他说,“你爸,陈建国,是我师傅。”
我爸?
我爸是个木匠,在我很小的时候,因为工伤事故去世了。
他说的,是我爸?
“我爸……他……”
“没错。”林海点点头,眼神里流露出一丝伤感,“你爸当年对我恩重如山。我刚出来学手艺的时候,家里穷,吃不上饭,是你爸收留了我,把手艺倾囊相授。”
“后来……他出事那天,我也在场。”他的声音低了下去,“那根木头砸下来的时候,是他把我推开了。”
我的眼泪,一下子就涌了上来。
这些事,我妈从来没跟我说过。她只说我爸是意外。
“这些年,我一直在找你们母子。但你们搬了家,我找不到了。”林海叹了口气,“直到前几天,我一个老乡说,在人才市场看到了一个叫陈驰的年轻人,简历上写的籍贯和我很像。我让他想办法把你的简历要了过来,一看,果然是你。”
原来是这样。
原来不是什么骗局,也不是什么天上掉下来的馅饼。
是父亲十几年前种下的善因,在今天结出了果。
“叔叔……”我哽咽着,叫了一声。
“别叫叔叔,叫林叔就行。”他拍拍我的肩膀,“孩子,这些年,苦了你了。”
我再也忍不住,眼泪决堤而出。
这些天所有的委屈、辛酸、绝望,在这一刻,全都找到了宣泄的出口。
那天,我和林叔聊了很久。
他聊我爸,聊他当年怎么从一个小学徒,一步步打拼到今天。
他开了个家具厂,后来转型做了智能家居,公司不大,但做得有声有ud。
“你爸当年最大的心愿,就是你能有出息,不像他一样,一辈子当个苦哈哈的木匠。”林叔说,“现在,我来替他完成这个心愿。”
“你明天就来上班吧。”他看着我,“就当我的助理。从头学起。我不要求你多聪明,但你必须跟你爸一样,踏实,肯干。”
我用力地点头。
“工资的话,我先给你开一万。够不够?”
一万?
我当时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。
我以为我听错了。
“林……林叔,太多了……我什么都不会……”
“不多。”他摆摆手,“这是你应得的。你爸拿命换来的,不止这个价。”
走出那栋写字楼的时候,阳光正好。
我抬头看着天空,觉得那阳光前所未有地温暖。
我捏着口袋里那张薄薄的访客卡,感觉它有千斤重。
我突然想起了那个算命先生。
三个月,发大财。
这算不算?
对我这个穷途末路、连饭都吃不上的人来说,一份月薪一万的工作,和一个愿意真心栽培我的长辈,这比任何“横财”都要珍贵。
我回到白石洲,第一件事就是去楼下的小卖部,买了一堆吃的。
泡面,火腿肠信康优配,鸡爪,啤酒。
我把老刘叫了过来,把阿飞也叫了过来。
老刘替我高兴,一杯接一杯地敬我。
阿飞看着我,眼神复杂:“行啊你,兄弟。真人不露相啊。”
我笑了笑,没多解释。
那天晚上,我喝多了。
我好像把我这二十二年的人生,都重新过了一遍。
我哭了,也笑了。
第二天,我正式去上班了。
我换上了公司发的工服,坐在林叔办公室外面那张属于我的办公桌前,感觉一切都像在梦里。
李经理,就是那个HR,成了我的直属领导。她给了我一大堆资料,让我熟悉公司业务。
我看得头都大了。
那些商业术语,市场分析,财务报表,对我来说就像天书。
我这才明白,我和那些写字楼里的白领,差距到底有多大。
但我没有气馁。
我把林叔的话记在心里:踏实,肯干。
我每天第一个到公司,最后一个走。看不懂的就抄下来,晚上回去查资料,或者厚着脸皮去问同事。
同事们对我这个“空降兵”态度各异。
有客气的,有疏远的,也有在背后指指点points的。
“听说了吗?新来的那个总裁助理,老板的远房亲戚。”
“怪不得呢,什么都不会,一来就坐这个位置。”
“关系户呗,咱们公司也免不了俗。”
这些话,我都听到了。
我不生气,也不辩解。
我知道,我唯一能做的,就是用行动证明自己。
林叔很忙,经常出差。
但他只要在公司,就会把我叫到办公室,像师傅带徒弟一样,一点一点地教我。
从怎么看合同,到怎么跟客户打交道,再到怎么管理团队。
他对我要求很严。
有一次,我给他整理一份会议纪要,因为粗心,把一个数据弄错了。
他把我叫到办公室,当着几个部门主管的面,把我骂得狗血淋頭。
“这点小事都做不好,我怎么放心把更重要的事交给你?你对得起你爸吗?”
我当时脸涨得通红,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
但我心里没有半点怨恨。
我知道,他是真的为我好。
从那以后,我再也没有犯过类似的低级错误。
工作渐渐上了正轨,我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我从白石洲那个八平米的单间搬了出来,在公司附近租了一个正经的一室一厅。
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,有阳光能照进来的窗户。
我第一次领到工资的时候,留下生活费,剩下的全都打给了我妈。
我妈在电话那头哭了。
她说:“儿啊,妈就知道你会有出息的。”
我拿着电话,眼圈也红了。
我没告诉她林叔的事。我怕她伤心。
我只说,我找到了一个好工作,遇到了一个好老板。
日子一天天过去,离算ag命先生说的“三个月”期限,越来越近了。
我几乎已经把这件事忘了。
因为我现在的生活,已经不需要那种虚无缥ove的希望来支撑了。
我每天都很忙,很累,但很充实。
我能感觉到自己在飞速成长,像一块海绵,疯狂地吸收着养分。
然而,命运似乎总喜欢开玩笑。
就在那三个月期限的最后一天。
出事了。
那天,林叔去外地参加一个重要的项目招标会。
我是留守在公司。
下午三点左右,我接到了李经理的电话,她的声音带着哭腔。
“陈驰,不好了!林总……林总出车祸了!”
我当时整个人都懵了。
我赶到医院的时候,林叔已经被推进了手术室。
李经理和几个公司高管都在外面等着,个个脸色惨白。
我从李经理断断续续的叙述中,大致明白了情况。
林叔在去机场的路上,为了躲避一个突然窜出来的孩子,车子撞上了护栏。
对方司机肇事逃逸了。
林叔伤得很重,颅内出血,还在抢救。
我站在手术室门口,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。
这个男人,他把我从泥潭里拉出来,给了我新生。
他是我父亲的延续,是我的恩人,也是我的精神支柱。
如果他有什么三长两短,我该怎么办?
手术持续了七个多小时。
那七个小时,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七个小时。
医生出来的时候,告诉我们,手术很成功,但林叔因为大脑受到重创,陷入了深度昏迷。
什么时候能醒过来,不好说。
可能是一个星期,也可能是一个月,也可能……是一辈子。
这个消息,对整个公司来说,无异于晴天霹雳。
林叔是公司的灵魂。他倒下了,公司这艘船,就没了舵手。
第二天,各种坏消息接踵而至。
我们正在竞标的那个大项目,黄了。
几个合作了很久的供应商,开始催讨货款。
银行也嗅到了危险的气息,派人来公司考察,暗示可能会抽贷。
更要命的是,公司内部也开始人心浮动。
几个跟着林叔一起打江山的老臣子,开始有了自己的小算盘。
我每天守在林叔的病床前,看着他毫无生气的脸,心里刀割一样疼。
公司那边,李经理一个人焦头烂额,勉力支撑。
我知道,我不能再这样消沉下去了。
林叔把公司交给我,是信任我。
我不能让他醒来的时候,看到一个烂摊子。
我回到了公司。
我召集了所有部门主管开会。
当我坐在林叔的位置上时,下面一片窃窃私语。
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。
我一个22岁的毛头小子,凭什么?
一个销售部的老资格,姓王,第一个发难:“陈助理,现在公司群龙无首,我们是不是应该先从几个副总里,推选一个出来主持大局?”
他这话,立刻得到了几个人的附和。
我看着他,平静地说:“王总,林总走之前,授权我全权处理他住院期间的公司事务。授权书在这里。”
我把林叔之前以防万一签好的授权书复印件,发给了每一个人。
会议室里安静了下来。
“我知道,在座的各位,都是公司的元老,是我的前辈。”我站起来,给他们深深鞠了一躬。
“我陈驰,资历浅,能力有限。但我今天坐在这里,不是为了我自己的权力,是为了保住林总一辈子的心血,为了保住我们在座各位的饭碗。”
“现在公司是什么情况,大家比我清楚。如果我们自己先乱了,那公司就真的完了。”
“我恳请各位叔叔伯伯,看在跟林总多年交情的份上,帮我一把,帮公司渡过这个难关。”
我的话, शायद触动了他们。
毕竟,他们中的大多数,都是跟着林叔一路苦过来的,对公司有感情。
那个王总沉默了半晌,说:“你想我们怎么做?”
“稳住。”我说,“稳住供应商,稳住客户,稳住银行,稳住我们自己的人。”
接下来的一个月,是我人生中最黑暗,也是成长最快的一个月。
我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,医院和公司两头跑。
白天,我在公司处理各种焦F头烂额的事务。
为了稳住供应商,我挨个上门拜访,签下了个人担保的还款协议。
为了稳住银行,我把我名下唯一的资产——林叔给我买的那套小公寓,拿去做了抵押。
为了稳住人心,我拿出了自己所有的积蓄,准时发了那个月的工资。
晚上,我就去医院守着林叔,给他擦身,跟他说话,把我白天遇到的所有事,都讲给他听。
我跟他说:“林叔,你快点醒过来吧。你再不醒,我真的撑不住了。”
我瘦了二十斤,整个人都脱了相。
李经理看我这样,心疼得直掉眼泪。
她说:“陈驰,你别把自己逼得太紧了。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”
我苦笑。
好吗?
我不知道。
我只知道,我快到极限了。
公司的资金链,马上就要断了。
如果下个月,再没有新的资金进来,公司就要破产了。
我把所有能想到的办法都想了,所有能借钱的朋友都借了。
没用。
那个缺口太大了。
我再次感到了那种熟悉的绝望,比在白石洲啃泡面时,还要深沉的绝望。
那天晚上,我又一次坐在林叔的病床前。
我握着他冰冷的手,终于崩溃了。
“爸……”我趴在床边,第一次这样叫他,“你看到了吗?你儿子没用……我守不住你的心血……”
我哭得稀里哗啦,像个迷路的孩子。
就在这时,我感觉我的手,被轻轻地动了一下。
我猛地抬起头,看到林叔的眼皮,在微微颤动。
“林叔?”我试探着叫了一声。
他的手指,又动了一下。
我赶紧冲出去叫医生。
经过一系列检查,医生告诉我,林ve是一个奇迹。
林叔的生命体征开始恢复,意识正在苏醒。
他醒了。
虽然还不能说话,不能动,但他能听懂我说话,会用眨眼睛来回应我。
我喜极而泣。
只要他能醒过来,比什么都重要。
公司破产就破产吧,大不了,我再回去当木匠,我养他。
我把公司快要破产的消息告诉了他。
我以为他会很激动。
但他没有。
他只是静静地看着我,然后,非常缓慢地,眨了一下眼睛。
一下,代表“是”。
两下,代表“否”。
我问他:“林叔,你是不是有办法?”
他眨了一下眼睛。
然后,他用尽全身力气,抬起手指,颤颤巍巍地指了指他办公室的方向。
我立刻明白了。
我冲回公司,冲进他的办公室。
我在他的办公桌、书柜里疯狂地翻找。
最后,在一个上锁的抽屉里,我找到了一个保险箱。
密码,是我爸的生日。
打开保险箱,里面没有我想象中的现金或者房产证。
只有一个很旧的笔记本,和一份……股权转让协议。
我翻开那个笔记本。
上面,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一些名字和数字。
那是林叔这些年,以私人名义,资助过的所有贫困学生和参与过的慈善项目。
每一笔,都清清楚楚。
总金额,是一个我不敢想象的天文数字。
原来,他赚的钱,大部分都用在了这里。
我再看那份股权转让协议。
上面写着,如果他遭遇不测,他名下所有的公司股份,将自动转让给一个叫“山海基金会”的慈善机构。
而我,将作为这个基金会的执行人,拥有这笔股份的代理管理权,直到我年满35岁,或者,他指定的继承人出现。
我拿着那份协议,手在抖。
我终于明白了他的一切安排。
他从没想过把公司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。
他把它当成了一个工具,一个用来帮助更多人的平台。
而他选择我,不仅仅是因为我爸的恩情。
他是在我身上,看到了他想要的品质:善良,坚韧,知恩图报。
他是在用这种方式,考验我,也是在保护我。
如果我心术不正,想要侵吞公司财产,这份协议会让我的所有企图落空。
如果我能守住本心,这份协议,就是我拯救公司的最后一张王牌。
因为,“山海基金会”的背后,站着几个非常有实力的企业家,他们都是林叔多年的至交好友。
有了这份协议,我就能名正言顺地去找他们求助。
我拿着文件,冲回医院。
我跪在林叔床前,泣不成声。
这个男人,他算计好了一切。
他用他的智慧和善良,为我铺平了最后,也是最关键的一条路。
后来的一切,就顺理成章了。
我联系了基金会。林叔的朋友们得知情况后,立刻伸出了援手。
资金很快到位,公司的危机解除了。
那些摇摆不定的供应商和客户,也重新恢复了合作。
公司,保住了。
三个月后,林叔已经可以下床走路,进行康复训练了。
虽然说话还有点含糊,但思路已经完全清晰。
他把所有人都叫到会议室,当众宣布了两件事。
第一,公司将划出30%的利润,注入“山海基金会”,用于慈善事业。
第二,他正式任命我为公司总经理,全权负责公司的日常运营。
会议室里,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。
这一次,那些掌声里,没有了质疑和嫉妒,只有真心的钦佩。
我站在林叔身边,看着他斑白的两鬓,心里百感交集。
那天晚上,我一个人开车,又去了那个天桥。
那个算命的摊子,已经不在了。
也许他早就收摊回家了,也许他从来就没有真的存在过。
我站在天桥上,看着脚下川流不息的车河,和远处辉煌的万家灯火。
三个月,发大财。
算命先生的话,应验了。
我确实得到了一笔“大财”。
但这笔财,不是从天而降的彩票,不是投机取巧的偏门。
它是我父亲用生命换来的善缘。
是林叔用半生心血搭建的平台。
是我自己在这三个月里,用血泪和汗水拼出来的尊严。
这笔“财”,不是金钱,是成长,是责任,是明白该如何堂堂正正做人的道理。
我对着空无一人的天桥底,深深鞠了一躬。
谢谢你,算命先生。
也谢谢你,深圳。
谢谢你让我明白,这个世界上,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横财。
所有的运气,不过是善意的积累和不屈的自己。
我转身,发动汽车,汇入了那片璀璨的灯海。
我知道,我的路,才刚刚开始。
富腾优配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